关于流传的一些暴雨过后,一名援沪方舱医生写下日记,“希望我熟悉的魔都快回来!”和描述隔离外面下雨的心情的案,想必很多人都是比较想了解的,下面就让小编来讲解吧!
4月13日,上海昼夜倾盆大雨。对于支援张江高新方舱医院的河南省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治医师史卞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大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这一夜,他们两次冒着职业暴露的风险,在雨中狂奔;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们用自己的体温来烘干衣服。大雨导致交接班严重延误,司机返程时不得不减速。当他们终于回到松江的酒店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零五分了。此时,大家已经近10个小时没有喝水了。
醒来后,石扁用文字记录了这一夜。最后,她写道“我们的一生要经历无数个夜晚,无论是平淡的、快乐的、还是孤独的。这样风风雨雨、勇敢的夜晚,也许会成为一生的回忆。即使风雨飘摇,只要心中有光,我们就能迎着东方的第一缕曙光,走出花开的小路。”
河南救援医疗队已经在方舱医院度过了16个日日夜夜,在方舱医院的时间总体上是平淡而平静地度过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患者病情严重。医疗救治的主要工作是给患者开药、进行核酸检测、提供一日三餐,及时安抚患者情绪。工作量看似不大,但大家必须克服穿防护服、通勤等不便,日常个人防护方面也比我们预想的要繁琐。
史卞向晨报编辑讲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日常生活,这或多或少是每个收容所工作人员都在经历的。
抗击疫情前线关键是控制感染
张江高科方舱医院由10栋建筑组成,于4月7日晚移交河南省医疗救助队管理运营。方舱内驻扎有来自河南7家大型医院的约1500名医护人员。史卞来自河南省肿医院。医院派出近190名精锐医护人员,支援8号楼1000余名患者。4月16日,首批80余名患者解除隔离;一天后,100多人拿到了出境证明。但新病人不断涌入。
4月2日晚,石卞和她的同事们收到了支援通知,第二天早上7点大家就到医院集合。我接受了两个小时的感染控制培训,分发物资,并于9点30分前往机场。他们乘坐下午的航班,两个小时后抵达上海。
时卞的老师来送行
时卞的老师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前来送行。两年前武汉疫情爆发时,全院动员医生护士报名。当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的老师报名了。但当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专业要求更严格,派出的医生都是来自综合医院的呼吸专科医生。
施卞和她的同事们此前几乎没有在一线抗击疫情的经验。去年夏天,郑州爆发疫情,她只参与核酸检测。无论医生是否有一线抗疫经验,感染控制都是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所谓感染控制,就是指感染控制。在方舱医院,每个医疗队都配备了多名感染控制人员。他们是医护人员安全和方舱医院正常运转的保障。
河南省肿医院的医护人员平时在8号楼办公。4号楼是专门的穿脱区域。设有防护服穿脱通道,分为第一脱衣区和第二脱衣区。定期穿脱防护服是感染控制的重点,脱脱环节更是严格。
下班后,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从4号楼前往8号楼,在第一个起飞区进行双手消,然后进入房间。脱防护服时,外层衣服不得与内层衣服接触。脱防护服时,必须将防护服向外卷起,然后脱掉鞋套和防护面罩。随后,进入第二起飞区,摘下帽子、口罩,消双手,再戴上干净的口罩。
穿脱衣服时,感染控制老师在场,注意检查脚步是否凌乱,封闭是否严密,脱衣时地面是否有污渍,是否有异味。“现在都安装了监控,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你的头上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哪一步错了。”
另一个预防点是返回酒店后。石卞向酒店要了一把椅子,将外套挂在椅子上,然后进了房间。大衣里面是手术室穿的绿色洗手服。进入房间后,立即脱下这套衣服放入盆中,用消液浸泡,再用另一个盆盖住。然后摘下口罩和帽子,在此过程中保持闭眼。“把脱下来的东西全部放进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绑起来放到屋外。然后赶紧洗澡,冲洗头发和鼻子,这个过程中还是闭上眼睛。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但也不能懈怠,控制感染非常重要。”
一名50岁的男性患者向她发出警报
4月3日抵达后一周,医疗队忙于整理舱内设施、准备物资、开展空舱作业。
“收容所装修得比较仓促,刚到的时候,很多设施和物资都没有准备好。进去后,指挥部告诉我们物资和药品要怎么分配。刚开始的几天,大家都跑上跑下,分发物资。回到搬运工那里。”
一栋大楼有四层,每层都是一个病房。每个病区有200多张床位,被子、床垫需要从一楼运到每个病区的床位。这些任务由护士完成。空舱运行了三天,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趟航班,一切才准备就绪。他们还申请了患者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如卫生纸、湿纸巾、拉拉裤、婴儿奶粉等,现在护士站都备货充足。
4月10日晚,8号楼开始收治第一批患者。“那天晚上我没有值班,所以我看到群里到处都是消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混乱。”史卞回忆道,“群里大家纷纷询如何给患者发放腕带、如何登记信息、如何扫码……二楼共有250张床位,170多名患者当晚就被收治了。从第二天开始,秩序逐渐恢复。”
每人每天轮班,每次4小时。施变的第一班时间是4月11日下午4点至8点,当天约诊了30名有症状的患者。“病人普遍都很焦虑。他们说,‘医生,我咳嗽,喉咙痛。我感觉很不舒服!’你测量他们的心率和手指脉搏血氧,只要氧饱和度大于93,我们就会判断病人基本上不会重症,因为他的肺功能还是很好的。”
在所有的病人中,有一个让她感到惊慌。他是一名50岁的男子,心率达到每分钟125次。患者表示,他的视力模糊,舌头感觉僵硬。
“我一看到病人有重症风险,就联系了指挥部,指挥部说先请专家会诊。——整个方舱里都有专家组,所以我给专家打电话“团队。他们详细询了这位患者的情况,因为我们舱内只有基本药物,如果患者肺功能继续下降,就会被转入医院。我们决定先维持观察。”
1/3的时间花在安抚病人的情绪上
4月12日,时卞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病人,发现“还是老样子,心率还在110到120之间”。
她立即向指挥部汇报,坚持必须将病人转移。“因为我们作为医生最害怕的就是耽误病情。”指挥部给出的反馈是,已将情况报告给指定的周浦医院,但由于医院没有床位,暂时需要等待。
时卞向患者询疫苗接种情况。“这个病人之前打过两次针,没有打加强针,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另外,他自己也很着急,这也可能会加重症状。这种焦虑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不停地去办公室找时边,护士很无奈,“时医生,这个病人又来了。”时卞站在病人床边安慰他,“我说,‘你昨天才进来,现在不严重,观察一两天就可以了。’但说实话,我们的医疗很担心。”那两天的时间里。”
在收容所里大约1/3的时间都花在安抚患者情绪上。“很多病人感到焦虑。他们说,‘医生,我需要尽快康复!请帮助我!’“医生,昨天开的药没有作用,我喉咙还痛,还咳嗽。”我们只是安慰他们,解释一下这个药的具体作用。“你看你现在的血氧饱和度和心率都非常正常,肺功能也很好,不可能像你这样病情严重,所以你应该放松一点,吃喝该吃的喝,每天喝,检测核酸,说不定有一天就会转阴。”
4月13日危险解除。“当天我从晚上8点工作到12点,一接班就去看病人,看到他的血氧饱和度已经达到了98,心率也下降了。”到了80多,我终于松了口气。”4月17日,患者收到第二份核酸阴性报告,即将出院。
收容所医生的主要职责是开药并判断病人是否有可能病情严重。史卞坦言,“这其实不是我们的治疗范围,但自武汉疫情以来,我们所有的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在进行关于COVID-19治疗和防护措施的培训。《第九版COVID-19诊疗方案》”写得也很清楚,看完就知道了。
实际情况与很多方舱患者描述的不同。这里可不仅仅只有莲花清瘟。“我们会给患者开一些对症药物,比如止咳药。对于那些喉咙痛严重的患者,我们会加一些消炎药和一点口服阿莫西林。”
尽管收容所里的所有患者症状都很轻微,但很多事情都不确定。“前天医生值班时,一名30多岁的年轻患者突然陷入昏迷,当时大家真的很害怕,紧急给他做了心电监护,测量了血压、血糖。幸运的是,过了十多分钟,病人的意识恢复了,直到昨晚,大家才把监控撤掉。
我打开手机,给司机播放了《天路》。
从4月13日晚上到4月14日凌晨,石卞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下午6点20分,公交车在松江酒店门口接他们,1小时10分钟后到达收容所。由于带入机舱的物品会造成污染,所以没有人带雨伞。我把塑料袋套在身上,把塑料袋套在脚上。等了几分钟,见没有班车,我就冒着雨跑向8号楼。
“那种感觉很难忘,风雨太大,生怕屏幕被吹掉,我用力把头埋进去,弯着身体往前跑,但外面的隔离衣还是湿的。还好。”“,走了几十米就看到了,有班车,我们就站在路中间挥手叫停,就坐了仅有的两个座位。”
石卞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红色路线为进舱路线,蓝色路线为下班返回路线。单程大约需要10分钟。
大雨导致巴士延误。石卞和她的同事们本应14日0点00分下班,却等到了0点45分。出了大楼后,我仍然一路狂奔,冒着生命危险,冲向4号楼。
“大风差点把我的面罩吹掉,口罩已经湿了。我很紧张,害怕口罩湿了之后职业暴露。我一路跑着,弓着身子,把头埋在了自己的衣服里。”“我的胸部,身体呈90度弯曲,最外面的隔离衣和鞋子都湿透了,我们终于到达了4号楼的穿脱区域。”
由于交接班延误,直到1点30分最后一人才上车。回来时,大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们开了1小时40分钟。收拾好东西后,我看了看时钟,已经04:00了。一个班次看似4个小时,但从前一天晚上18:30出发算起,已经9个多小时了。
医护人员下班回来路上
接班团队由河南省肿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科副主任医师马东阳带队。当这支队伍离开机舱时,已经是14日凌晨5点30分了。“接班时是风雨交加的午夜,下班时是黎明。我们在公交车上,第二次用体温烘干衣服。我们查看手机,发现实时气温是14度,穿的衣服都是医院发的,裹着浴巾,穿着薄外套,大家又饿又冷,这是上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
马东阳也在朋友圈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负责接他们的司机此时已经累极了。从前一天晚上10点20分开始,他就一直在酒店和小木屋之间来回奔波,眼皮已经忍不住打架了。马东阳快步走到前排,打开手机给司机播放韩红的《天路》。
早上7点16分,马东阳的医护人员队伍终于到达了他的住处。大家纷纷与司机合影留念,作为此次旅行的纪念。
阔别十年,上海依然影响着我
方舱医院的工作量并不大,但医疗队员面临的一个重大题是,由于方舱院区不建议饮食,而且通勤至少要两个小时,很容易挨饿。最难的是凌晨4点到8点轮班的医生和护士。离开酒店的时候早餐还没有送来,回到酒店已经是十点多了。这意味着距离前一天晚饭后还有十多个小时。没有办法吃饭。
时卞胃不好。有一天,他吃得太饱了,肚子疼。“疼得我坚持不了半个小时,就在群里紧急求助。我们的后勤老师人很好,马上给我送了奥美唑,还叫了快递,已经快到了。”晚上11点了,反正送到了。”
这些吃惯了面食的医疗队员来到上海后,就水土不服了。严重时甚至开始腹泻。考虑到疫情期间无法制作新鲜面条,酒店为大家准备了方便面和馒头。从16号开始,酒店还为每个楼层配备了微波炉。下班回来后,可以将饭菜加热后再吃。
时卞这些天最想念的就是孩子们。她说“孩子是最大的弱点,现在只要有人跟我提起孩子,我就想哭。”她在电话里哽咽地说“我的大儿子,是我的女儿,今年6岁了。4月2日,我告诉她,我妈妈要去上海支援抗疫,那里的病非常严重。”不好,很多人生病住院了,我妈妈本来要去帮助他们的,她现在明白了。之后,幼儿园老师也会给他们画一些漫画,教他们一些防疫措施。我女儿一听就哭了。并说“妈妈,不要离开。如果你也
现在大家应该对暴雨过后,一名援沪方舱医生写下日记,“希望我熟悉的魔都快回来!”和描述隔离外面下雨的心情有所了解了吧,欢迎大家关注并收藏本站,谢谢各位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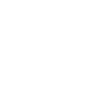


No Comment